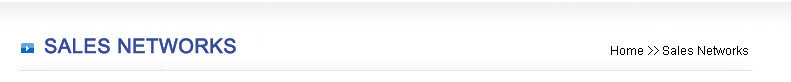“大器-茶里漆香”傳統(tǒng)生活美學(xué)的新表達
發(fā)布時間:2015-01-12 11:35:17 點擊次數(shù):3989
2015年1月9日,由紅坊沙龍主辦,紅橋畫廊承辦,“大器·茶里漆香”主題展覽在紅橋畫廊拉開序幕,展覽持續(xù)至2015年2月28日。本次展覽以“茶生活”為線索,將大漆、繪畫、家具等多元化的內(nèi)容有機的結(jié)合起來,以“用”為精神,在不同的情景中為觀者展現(xiàn)“漆藝”生活。
漆藝再創(chuàng)造:傳統(tǒng)和現(xiàn)代的對話
(福建)福州脫胎漆器是具有獨特民族風(fēng)格和濃郁地方特色的漢族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珍品,與北京的景泰藍、江西的景德鎮(zhèn)瓷器并稱為中國傳統(tǒng)工藝的“三寶”,享譽國內(nèi)外,曾被譽為“珍貴黑寶石”和“東方珍品”。2006年,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入選國家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。
據(jù)展覽的策劃人馬箐介紹說,該展覽的創(chuàng)意緣自于在過去的兩年中,上海紅坊文化發(fā)展有限公司為福州市政府連續(xù)策劃并承辦了兩屆“福州海峽創(chuàng)意設(shè)計周”,借此契機紅坊文化持續(xù)關(guān)注福州當?shù)貍鹘y(tǒng)手工藝的過去、現(xiàn)在與未來。在與漆藝大師的促膝長談和對“大漆”產(chǎn)業(yè)的深入調(diào)研中,不僅感嘆這項工藝的深邃與珍貴的同時,嘆息這一傳承七千年的技藝所面臨的窘境——漆畫行業(yè)空前繁榮,但作為生活用品的漆器卻缺乏創(chuàng)新。這不由激發(fā)了主辦方通過發(fā)掘“新”人推動“手藝再生”的想法,這里的“新”人并不僅僅指年輕人,而更多的是指從新的視角和新的理念去運用漆藝的人。
為此,紅坊文化組織了來自上海和北京的藝術(shù)家薛松、潘微、黃淵青、陳墻、曲豐國、吳永平與福州當?shù)氐拇笃崴囆g(shù)家陳建兵、劉經(jīng)峰共同合作,歷時一年創(chuàng)作完成了近五十件原創(chuàng)大漆器物,力圖在還原漆器作為生活器物本質(zhì)的同時,充分發(fā)掘大漆技藝的潛力,利用材料的特性進行應(yīng)用創(chuàng)新。
同時,此次展覽還邀請了現(xiàn)居上海的福州大漆藝術(shù)家趙建偉和沈也先生以及上海設(shè)計品牌多少、福州設(shè)計品牌紅點生活,其作品的加入深化了主題“茶生活”,為疾走于都市生活節(jié)奏中的人們創(chuàng)造靜思品茗的意境。
在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,跨界并不鮮見,它既跨越了藝術(shù)邊界,也是來自不同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方式的人們共同參與到各自不同場域、實現(xiàn)文化互動,并在此過程中實現(xiàn)對彼此行業(yè)的重新認識。
現(xiàn)居上海的福州大漆藝術(shù)家趙建偉一直致力于將脫胎漆器從傳統(tǒng)民俗陳列品變成當代生活用品。
他說,縱觀漆器歷史,盛于漢而衰于唐,一直都是貴族用品,難以走進平常百姓家庭,在宋代瓷器浪潮的沖擊下慢慢走向衰落和邊緣化,到了明清,漆器由實用轉(zhuǎn)向陳設(shè)裝飾領(lǐng)域,并一直延續(xù)到現(xiàn)在,即使變成當代生活用品,也不能普及,只能是奢侈品。
為此,他大膽運用福州傳統(tǒng)的脫胎技法,使用到古琴裝飾與修復(fù)上,反而碰撞出了不一樣的感覺:“恰恰我們做完以后,反應(yīng)非常好,整個音質(zhì)效果被全面提高。
在他看來,做漆器藝術(shù)作品,不管是當代、架上、還是器皿,對于傳統(tǒng)技藝的掌握還是很關(guān)鍵:“沒有傳統(tǒng)的底蘊為支撐,你無法完成很多現(xiàn)代的語言、技法與理念。福建漆畫會如此出名,其實也是有它的原因,正是緣自福州脫胎漆器傳統(tǒng)文化的基礎(chǔ),如果它沒有傳統(tǒng)支撐,也不可能走到現(xiàn)在。”
跨界漆藝:當代藝術(shù)家尋找新的表達
如何將古老的漆藝中融入當下的思維方式,這不僅是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傳承,也是一次新鮮的藝術(shù)嘗試,這意在建構(gòu)福州漆藝新的交流平臺,以現(xiàn)代回溯傳統(tǒng),用傳統(tǒng)探訪當下。然而如何將看似并不搭界的漆藝與當代抽象藝術(shù)成功結(jié)合,這也給這次展覽的參展的當代抽象藝術(shù)家們帶來了新挑戰(zhàn)。
在藝術(shù)家陳墻看來,嘗試漆藝,這其實是對于自身多年繪畫藝術(shù)習(xí)慣的一種突破:“繪畫的體驗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這種掌控中,我們唯一要突破的就是我們十幾年二十幾年的繪畫習(xí)慣,如何發(fā)揮創(chuàng)造力是對我們的考驗,之所以運用漆藝這種陌生的材料,實際上也可以擺脫我們十幾年的慣性思維模式,對于我們而言,它是一個新的東西。”
同時,這也是一種不同材料運用下的碰撞:“當然對于大漆的工匠來說,他們也是玩了十幾年、二十幾年,但是他們的想法跟我們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樣的,這就是一種反差,我們希望這兩者碰撞一起,我們希望在這個碰撞過程當中,能夠碰撞出火花來。”
在本次展覽中,陳墻將其繪畫中最具代表性的圓點元素,運用至整個大漆茶器的創(chuàng)作上,在他看來,這為傳統(tǒng)大漆生活器皿加入了當代語言,使其更適合現(xiàn)代生活美學(xué):“我們現(xiàn)在當代生活受歐洲的影響太重,大部分生活器也比較西方化,所以如果看傳統(tǒng)大漆生活器皿,它是很古老的東西,就跟紅木家具沒什么區(qū)別,那么它就和當代生活難以溝通融合。如果加入當代語言,就它的當代語言的這種介入,我覺得它有無限的空間。”
藝術(shù)家黃淵青則試圖在尋找自身繪畫作品與漆藝上的某種延續(xù)關(guān)系。在他的創(chuàng)意下,文字、大漆、古老的沉船木,有了一種新的延續(xù)之可能:“實際上根本上是在找某一種關(guān)系,這種延續(xù)是你平時思考的方法和特別的關(guān)系,比如說像我選擇木頭,選用什么樣的顏色,什么樣的形和它互相關(guān)系在這里,這表面說的是物理性的感覺,但是實際上里面有很多類似精神性的東西。實際它和繪畫一樣,就是我在尋找材料或者形式,和或者互相之間色彩互相的關(guān)系,如果能夠找到,我就覺得是好的,這種新的特點就是完全是個人化的。”
在藝術(shù)家潘微看來,對待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中未知的偶然性的不同態(tài)度,這是他們藝術(shù)家與傳統(tǒng)工匠中最大的區(qū)別:“工匠們他們是做一個比較規(guī)范的產(chǎn)品,我們創(chuàng)作的藝術(shù)品,好跟壞評判的準則不太一樣,我們幾個藝術(shù)家每個人取的材質(zhì)不同,做出的效果也不同。其實我們跟他們是兩個領(lǐng)域,工匠做漆器是工藝,所謂的工藝它有一個標準,工匠們不敢跨越標準,所以整體上說,他們做的東西都一樣,就是沒多大變化。但是藝術(shù)家們無所謂,又沒有一根很明確的線,過了也可以,不過也可以,只要達到我的口味,我感覺可以了就可以了。”
潘微介紹說,在歷時半年多的創(chuàng)作磨合期中,他們與工匠的配合首先在于藝術(shù)語言上:“配合當中首先就是我們自己的語言,要我們把自己語言的創(chuàng)作放進去,我們正好是本來在紙上的、布上的這種感覺用在了漆器里面,我的作品整體上說還是用文字,我需要將文字在這里面體現(xiàn)出來。”
習(xí)慣用“火燒”為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方式的藝術(shù)家薛松也在與漆藝的結(jié)合中找到了自己滿意的契合點。被火燒之后的沉船木與大漆工藝,令他的作品呈現(xiàn)出了另一種新鮮感:“我喜歡大漆的透明度,和打磨后多層層透的感覺,這個是漆藝比較多的,可以同時幾種顏色,打掉其它部分,然后保留第一層的色彩,這點跟我原來的作品有共通點。
“再塑經(jīng)典” 重新探尋當代新生活美學(xué)
民間工藝“跨界”進入當代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,這不僅是“再塑經(jīng)典”中的“再塑”,也是一種創(chuàng)新,是一種文化傳承后的再創(chuàng)造。
藝術(shù)家曲豐國表示,實用性、當代審美缺失,是漆藝發(fā)展中難以走入當代大眾生活的原因之一:“這其實很簡單,就是保留傳統(tǒng),不斷地把它傳統(tǒng)的樣式保留下來,然后他的生活一直跟它有關(guān)系,這個很重要。但是我們現(xiàn)在的漆器大部分都跟生活關(guān)系不大,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漆器藝術(shù)轉(zhuǎn)移到繪畫、轉(zhuǎn)到其它裝飾性的東西,它變得越來越小,就不可能形成一個普遍的大眾的生活的一個重要成分。跟生活的關(guān)系不大了,慢慢就可能普遍繼承這個東西就少了。”
“其實漆器本身它就很美,這種審美能力中國人早就有了,你的祖輩幾千年以前就有整個能力掌控和欣賞。漆器里面折射出的那種對時間性的認識,對整個亞洲的漆藝發(fā)展都貢獻很大,只是我們現(xiàn)在忽視了這種傳統(tǒng),但是實際這個很重要。這個傳承地會被大家慢慢地重新拾起來,會理解這種深厚的、有價值的這樣文化的傳承可能也需要一個時間和過程。”
薛松說,這次將傳統(tǒng)技藝加入不同的新鮮血液,是種不錯的合作方式:“因為傳統(tǒng)技藝,不光是漆藝,很多傳統(tǒng)技藝的包括刺繡等等,后來其實師承都是很單一的,都很難跳開固定框架。藝術(shù)家的大膽參與,跳出了師承與傳統(tǒng),創(chuàng)作了和現(xiàn)代審美更接近的作品。
“我覺得他們應(yīng)該感覺有點新鮮感,因為老在一個軌道上走,肯定沒有人沖擊或者刺激都會慢慢死亡,就是很難突破的。我覺得我們的觀念能夠激活這些傳統(tǒng),因為傳統(tǒng)工藝都有一套很成熟的辦法,也很好,只是怎么跟當代更結(jié)合,那可能就是我們參與的價值”。
黃淵青認為,正是因為藝術(shù)家和傳統(tǒng)的工匠都有會固定的某一種習(xí)慣,而跨界合作的創(chuàng)作方式就是試圖去改變某一種習(xí)慣,這種習(xí)慣被改變了以后,可能創(chuàng)作出來的東西會有一點不同,不同里面可能可以找到其它的可能,其實這樣的創(chuàng)新對他們傳統(tǒng)藝人應(yīng)該也是一個好處。
談及整個漆藝的創(chuàng)作與發(fā)展,在他看來,則是需要分兩條路走:“一個你如果真的把傳統(tǒng)都拋棄了,很可惜。師傅帶徒弟,一代代傳下去,這樣就等于活的標本,你可以看到過去的人怎么來做這個事情;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可以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,它怎么做的,兩個東西同時進行,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最理想的狀態(tài)。”
在潘微眼中,傳統(tǒng)技藝如果需要傳承,需要技術(shù)與材質(zhì)的新整合,并進入新的空間:“所謂空間,就是大家生活的空間,和現(xiàn)在傳統(tǒng)的漆器審美上、視覺上都有很大距離,所以需要把這些材質(zhì)重新整合一下進入新的空間。
縱觀中國民間工藝之所以遭遇生存困境,皆是因為與現(xiàn)當代生活脫節(jié),無法進入主流大眾審美,而如果想讓藝術(shù)品”越是民族的,就越是世界的“,在當下,則必須要在”民族“與”世界“之間架起創(chuàng)新的橋梁,使之以全新的姿態(tài)與現(xiàn)代生活緊密結(jié)合。在傳統(tǒng)與當代該如何更好的結(jié)合的問題之中,民間工藝在融合現(xiàn)代理念下能否獲得新生,并迎來更大的發(fā)展空間,盡管這種嘗試,還處于一個初級的階段,但嘗試就是一種進步。
如何讓民間工藝與現(xiàn)代當代藝術(shù)結(jié)合,重新探究民間工藝的發(fā)展之路,從而啟迪出新的創(chuàng)作智慧,這次的展覽則做出了一次有意義的嘗試。

 閩公網(wǎng)安備 350520302001781號
閩公網(wǎng)安備 350520302001781號